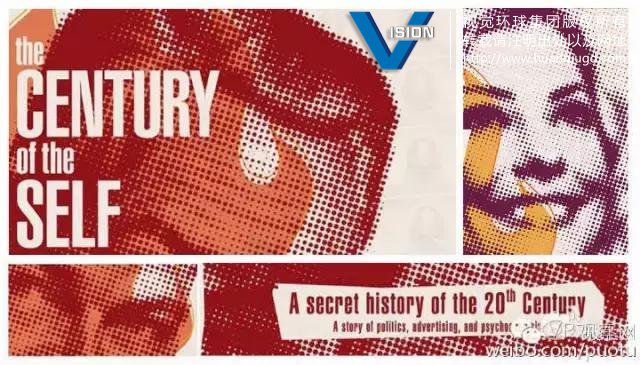VR与数字成本主义:多媒体展厅谁的虚拟?谁的现实?(2)
时间:2016-08-18 17:35 来源:视觉环球 作者:展厅设计编辑 点击:次
“共情”(emphathy来源于古希腊语ἐμπάθεια empatheia,由ἐν (en),“在”和πάθος (pathos), “passion” or “suffering”,“感情”或“遭遇”构成)由诗歌引起,没有任何特别的影响。这里的危险在于“共情”一词与使用“第一人称视角”体验故事的能力混淆了起来。 共情需要理解他人的情感状态,而非仅仅体验他们的所见,所以VR不能描述为共情机器,而应仅仅定义为第一人称视角体验工具。 目前,我们正见证着娱乐型或者人道主义型VR项目的发展。这种两极化的定义其地位的观点可能会模糊掉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在以第一人称视角身临其境之前,早已经用拥有技术、制作并发布内容的制作商或者企业的视角来看虚拟现实了。 当价值近50个亿的公司,如脸书、索尼或者谷歌,生产着虚拟现实的主要内容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它是否提供了一个精心挑选过的框架(然而它声称提供了真实可信的360度视角),就像摄影新闻并不需要声称真实性,只因为反映的就是现实;或者像联合国这样的政府组织在为拍摄一部有关难民的纪录片筹集资金的时候,我们要想想它是否站在难民的角度。 以《锡德拉湾上空之云》为例;一个难民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拍摄关于他们自身的虚拟现实纪录片吗?
《锡德拉湾上空之云》由联合国委托gaboarora和chrismilk制作而成。体验者佩戴一副大“眼镜”和拥有中英文双声道的耳机,立即进入一位名叫sidra的叙利亚年轻女孩的日常生活 最近TED上一个关于VR和共情的演讲宣称“虚拟现实如同真实”,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人类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些话让人不安。难道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最好方式不是我们亲身与难民相处在帐篷下么。 美洲印第安人有一句谚语:“要想评判一个人,先穿他的靴子走上一里路。” 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本身就是长久以来叙事带有偏见的绝佳例子。一直以来美国的历史是由定居的殖民者书写的,如今的土著居民在奋力让全世界人意识到他们被大规模灭族的故事。 正如故事讲述中体现的共情,我们最好围在火边闲聊故事或者在现实生活中的酒吧里对陌生人倾诉。 “很快,我们就会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能身临其境一般地分享和体验全部场景。想象一下,只要你愿意,就能坐在篝火边,同时和朋友一起闲逛。”(扎克伯格,2016) “Oculus Rift与其说让我们作为个体聚在一起,不如说让我们一起孤单。”(雪莉•特克尔,《一起孤单》,2012) 由社交孤立的工具变为宣传工具的虚拟现实,人们视VR为一种主动的娱乐形态,但我认为它是最被动的娱乐工具。 虚拟现实的体验完全夺走了观者的感觉。恰恰与之相反的是,假如阅读一本书或参观一个美术馆时,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距离和空间来组织他的想法,形成自己的观点。 事实上,虚拟现实的完全仿真是一种商品,令我们的意志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面对大量信息,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这片大海中航行,但却没有空间去提出问题,或“填补空白”。 我们不能由此激发想象力;相反,我们是屈服于虚拟现实。 “仅仅将虚拟现实看做安抚世界上贫困人们的工具,我们的想象力就被可怕地限制了。这像西方人的一个幻想,他们以为一项新技术就能解决一个他们尚未真正理解的问题。”(朱克曼,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体中心主任) 一种归企业所有的机器,并不可能令我们更有人情味、联系更紧密。它只会让人与人之间缺乏所需的“真正的”交流,彼此更加孤立。而且,在工作中我们也更多是以一群个体,而非一个集体的身份被对待。而在那些想借此传播自己观点和价值观的人的手中,仿真性让它成为一种“被动体验”,而非想象中的“互动”或者更有力量的东西。 VR就像其他媒介一样,用来说服人们、操纵思想,威胁着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那恰恰是民主本身的基础。亚当·库尔提斯的纪录片《探索自我的世纪》,讲述了企业怎样利用弗洛伊德的发现和媒介,通过欺骗性的技术手段引起人们无意识的恐惧和渴望,让他们想要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社交网络兴起,自拍时代出现,个人主义盛行,社交纽带和集体关系网遭到侵蚀,更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大家都自行其是。
《探索自我的世纪》 (责任编辑:环球编辑) |